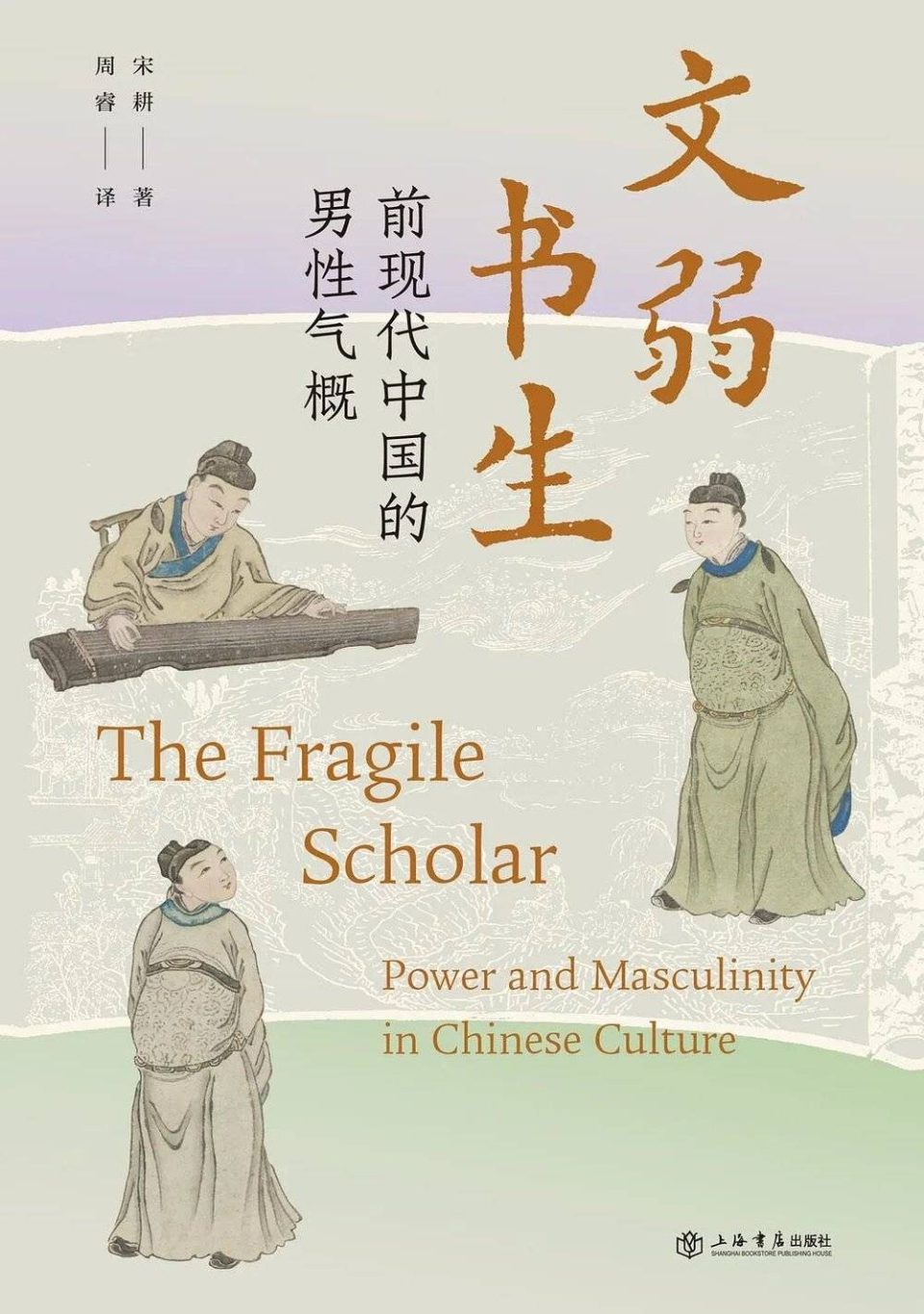1
读宋耕教授 《文弱书生: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 一书,是一趟自我疗愈之旅。之所以如此说,跟我自身的经历有关:我从小就是一个文弱的男生,经常待在家里看书,不喜欢跟别的男孩子玩那些在我看来很暴烈的游戏,也无法融入他们的小集体里,他们因此嘲笑我跟个女孩子一样,「不像个男人」。这样的评价让我深感自卑,很迫切地想要改变自己的行为,从而成为他们眼中真正的 「男人」。可是什么样的男人,才算是有男子气概呢?这给我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当我成年之后,我发现有不少男性友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和困惑。与此同时,放眼整个社会,从校园里男孩子太过柔弱,到娱乐圈里 「小鲜肉」 形象流行,「男生不像男生,女性不像女生」 成了很多人痛砭时弊的焦点,并大声呼吁开展 「正确」 的性别教育。那么问题来了,正确与否的标准如何去判断?这样的焦虑又是如何兴起的?这本书可以说给出了相当深入的研究。
学者大卫·D. 吉尔默在他的人类学著作 《发明男性气概》 一书中通过考察不同人类文化中的男子气概的观念来总结 「男子气概的普适性原型」,其结论是并不存在这样的结构或原型,因为男性特质概念在不同的文化中有天壤之别。宋耕也指出霸权男性气质并非与生俱来、放之四海而皆准,它是特定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产物,服务于父权制与男性社会主导地位,且各文化中男性气质均为话语建构,存在于特定空间,需以去西方中心化、多元视角看待性别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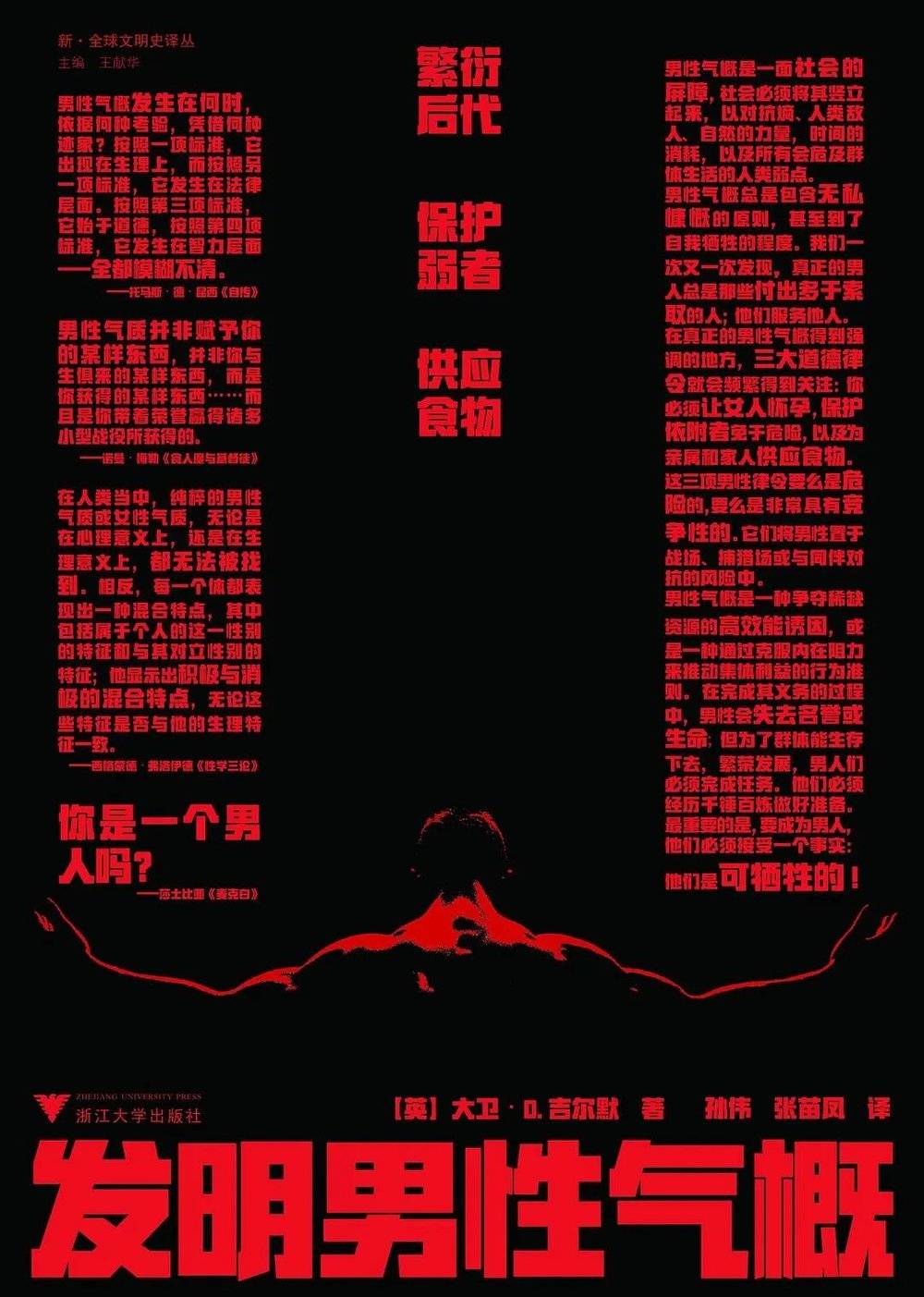
具体到中国,宋耕在本书序言中直言道:「我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单一而纯粹的 『中国男性气质』(Chinese masculinity)只能是一种想象。当代中国社会的男性气质与男性形象日益多元化,既受到商业文化以及西方、日韩流行文化的深刻影响,也与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 换言之,困扰我以及很多男性的 「什么是真正的男人」,并无标准答案,或者说每一种尝试给出的答案都如作者所言,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正如学者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性别既是建构性的,也是表演性的」。明白这一点后,我们也就可以从这种话语的压迫中抽离出来,冷眼看它是如何建构起来的。
一种观念的兴起,绝不是短时间内一蹴而就的,它一定有其渊源。宋耕在研究时发现:「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仍然对性别话语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近年来保守主义思潮和父权制的回归就是这方面的印证。」 所以,他想尝试贯通传统与现代,倡导对男性气质这一课题进行跨学科、跨历史、跨文化的研究。
如何去 「跨」 呢?必须找到合适的研究对象,才能实现其研究目的。这时,他注意到中国传统戏曲中的文弱书生形象,在西方人的眼中,这就是妥妥的 「缺乏男子气概」 的标志。而在当代很多不懂得欣赏戏剧表演的国人看来,看着台上那些举止妩媚、假嗓吟唱的白面小生扭扭捏捏地表演,也会认为太 「娘炮」 了。可前现代的中国人不这么看,宋耕指出:「尽管这一形象令今天的中西读者联想到柔弱女气,但 『才子』 却代表了中国传统理想型异性恋文学话语中所有被期许的男性特质」。
2
中西方对男性气质界定逻辑存在明显的差异。在西方世界,以 「男/女」 二元对立为核心,男性气质定义多通过 「不该像个女性」 来判定,依赖与女性/他者/自然的对立关系界定独立个体主体性,「反娘炮」 是其主流男性特质核心价值,且二元对立充斥暴力等级关系,男/女二元性是社会关系与身份认同的根本源头。
而在前现代中国却并非如此,宋耕发现儒家经典和官修史书里的人物基本上是无性别的,不止于此,中国通俗小说与戏曲中的英雄,如果对比西方的同题材作品中的英雄,会发现他们一定程度上也是去性别化的。这是为什么呢?宋耕提出了他的思考,「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主要以阴/阳二分法来界定,但 『阴/阳』 的指涉面要比 『男/女』 更为宽泛」。这个论点初一看,在已经习惯了用 「男/女」 二分法来思考世界的当代人来看,的确有点难以理解。男不就是 「阳」,女不就是 「阴」 吗?为什么要说 「阴/阳」 的指涉面要比 「男/女」 更为宽泛呢?
其实,「阳」 与 「男」,「阴」 与 「女」,并非对应关系,更不能用二分法的思维来理解。因为阴和阳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具有流动性的关系,相互转化、彼此依存。宋耕认为,「在儒家文化中,尤其是汉代之后,儒家被尊为官方意识形态,阴阳常用以阐释权力等级中的不同地位。『阴阳』 是高度政治化的概念,所指的是决定人的社会关系,甚至内在意识的政治文化中不同的主体地位」。由此,他指出,「前现代中国的性别话语是基于权力关系而非基于性别差异,性别和政治权力往往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在这种性别建构的话语中,『女性气质』 和 『男性气质』 是在等级秩序中建构出来的空间,并且必须从儒家化的政治角度予以解读」。
打个比方,有个位高权重的大臣,在自己家里他就是 「阳」,他的下人就是 「阴」,而等他上朝后,高高在上的皇帝就是 「阳」,他就是 「阴」。作为他本人,在生理性别上一直是男,可处在权力关系里,他是 「阴 「是 「阳」,全看他面对的是谁,「『阴』 或 『阳』 都不是生命实体,而是社会和政治权力等级秩序中的一个可浮动交替的位置」。
可以感受得到,发现 「阴阳」 背后的权力关系,作者是非常兴奋的,「阴阳模式不但是解读性 (sex)和性征 (sexuality)的锁钥,而且有助于梳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唯有借助阴阳模式,才能更准细致地解释中国文学与文化中的 「阴柔之气」,也才能理解 「文弱书生」,何以代表前现代中国被期许的男性特质,「霸权支配性权力通过对身体的操控实现对社会的管治,文人书生理想化的身体对帝制君权而言是最为安全放心的,因为它总与驯柔、文职相关联,而与叛乱或逾矩相去甚远;因此,对身体的操控有益于维系一个稳定而传统的 『文』 化社会,并在中国历史上绵延数千年」。
这种特质的形成倘若要找出一个时间点,应该是在宋代,男性气概典范普遍转向文人书生型。他们饱读诗书,温文尔雅,好沉思,喜古玩,不再热衷去狩猎,也不会参与激烈的运动。相比之下,那些尚武的北方胡虏,多么无知,多么粗鲁,根本无法与中原的文人雅士相提并论,并由此生出文化的优越感来。
3
《大唐狄公案》 的作者、著名汉学家高罗佩指出,中国才子佳人小说戏剧中的大多数男主角,都 「被刻画成一个白脸窄肩、文弱多愁的少年书生模样,大多数时间都耽于书籍和花丛之间,稍不如意辄病如山倒」。这个观察是相当准确的。不论是看明刊本的插图,还是观看当今戏剧舞台上的小生扮相,都是面容姣好、瘦肩细腰。
最为典型的是 《西厢记》 里的张生,崔莺莺初次在庙会遇见他便忍不住夸赞,「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扭捏着身子儿百般做作,来往向人前,卖弄俊俏」。到了下一折,莺莺重申她倾心张生是因为 「他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这要是搁到古典西方的语境,张生如此长相和性情早就被嫌弃了,这哪里有一丁点 「男子气概」? 宋耕引用夏志清评论道,「他真是一点都不让人信服。对习惯接受更具主见的浪漫主义英雄的西方读者而言,他显得太过意志消沉、太易自我了结,剧末面对郑恒的横刀夺爱也表现得太庸懦无能」。
《西厢记》 是宋耕重点分析的文本,也是大家熟悉的经典作品。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其原因在于它为才子佳人类型戏剧和小说的情节书写以及人物塑造提供了范本,「此后的才子佳人浪漫传奇逐渐定型,在主题、人物和情节上鲜少变化:才子通常容貌清秀、气质优雅、举止得体,也耽于思慕、溺于情爱,并写得一手好情书;佳人则是娴静优雅、温婉动情、仪态端庄,适时亦能敏思笃行」。
此剧的情节大家想必也非常熟悉:张生在普救寺相遇相国小姐崔莺莺,一见钟情,后历经波折,崔莺莺之母不得已答应了他们两人的婚事,附加的条件是张生应试及第后,才能与崔莺莺完婚。当然结局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张生到京考中状元后,赶回来挫败了情敌郑恒,崔、张完婚。好一个大团圆结局,无论你翻看多少才子佳人题材的作品,这都是标配。
我忍不住做出一个反向的假设:如果张生进京赶考,没有应试及第,更别说高中状元,他该怎么办?其实宋耕给出了一种可能性,他认为在作品的最后,「从张生与莺莺之间的异性男欢女爱,转为张生与郑恒 (及其暗含的权力关系)的同性社交竞争」。
张生击败了同性的郑恒,最终抱得美人归,是 「以莺莺为胜果,而非为莺莺而取胜」。为什么呢?因为,「莺莺被物化为在竞技中赢取的奖品,用以证明张生在道德与智识上胜人一筹,并奖励张生书生气的男性特质。戏中的异性恋话语被纳入同性社交等级秩序的框架中」。也就是说,张生因为高中状元,在权力结构上远高于郑恒,所以崔莺莺是他竞争得胜后的奖励。反过来说,如果张生没有成功,那崔莺莺必然会嫁给郑恒,而他只能成为丧家之犬,被人嫌弃。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张生为了谋生,成了写才子佳人类型作品的人。宋耕一再提醒我们 「才子佳人」 这样的文学艺术母题其实就是男人写给男人看的,「反映男性的幻想与焦虑,以及男性世界的权力关系;往往带有政治隐喻或儒生对身世飘零的感叹」。而传统中国男性气概主要是在男人的 「同性社交」 世界中,通过同性之间的纽带和认可来确立的,而非在 「男/女」 二元对立中以女性为他者,通过女性的认可来构建。
细心的读者应该发现了一个略显诡异的事情:当张生与郑恒两个男人你争我抢之时,崔莺莺却是沉默的那一个。她在作品的前半部分有多主动,在最后的抢人大戏中就有多被动。在决定她命运走向的冲突中,她无能为力,沦为了男性相争的占有之物。最后,她与张生得以完婚,并不取决于她是否爱张生,而是因为张生在同性社交领域得胜了。崔莺莺此时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存在在男性的欲望之眼中。我们无从得知她对男性特质的期望是什么。
另外一方面,这类作品的作者显然将才华横溢的男主角视为文人自我标榜式的产物,「凭借引经据典而不是耀武扬威的男性表现形式,文人书生多以此来夸耀自己的男性气概」。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 「才」 特指 「诗才」,即作诗禀赋而非经世之才。我们常看到才子佳人类型作品中的才子,只要吟诗作赋,便能赢得芳心。甚至没有见面,只读过诗作,女子就已经倾慕不已。你看张生,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凭借文才便能大逞其能,与其说是取材于现实,不如说是文人的自我赏识。
最后,这类作品里的才子都会金榜题名,从 「才子」 摇身一变成了登堂入室的 「君子」。正如冯梦龙在 《情史》 序中所写:「虽事专男女,未尽雅训,而曲终之奏,要归于正。善读者可以广情,不善读者亦不至于导欲。」 一语道破 「才子佳人」 故事的思想特质。
看起来,才子佳人作品男女之情如何逾矩,如何挑战了礼制,到最后却都以才子高中状元,迎娶 (或者说赢取)佳人收尾,就像是淘气的小孩虽然屡屡闯祸,终究还是长大成人,变成了规矩的大人,「『才子』 仍然属于儒家话语 『君子/小人』 二元论中的 『君子』 范畴,注定被收编以 『君子』,从而由短暂的、私人的、『阴』 的世界,进入公众的、『阳』 的世界 (也就是符合官方话语的 『男性』 世界)」。
宋耕由此对比了贾宝玉的异同,他们都是 「情痴」,都能吟诗作赋,都长相俊美,但贾宝玉却不是真正 「才子」,因为,「『才子』 毕竟圈定在儒家男性特质话语体系之中,而贾宝玉却是超然于正统官方话语之外的 『他者』」。可以说,贾宝玉象征着全新男性主体性的出现,《红楼梦》 之伟大可见一斑。
《文弱书生》 一书的英文版最早出版于 2004 年,当时还少有人关注男性的性别研究,此书填补了在中国男性史研究上的空白。20 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围绕男性气质的讨论从未止歇,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将会持续下去。
我认为最要紧的,不是成为什么阳刚的男人或者温柔的女人,而是成为一个人,尊重每个人的个性,让他们活成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那才是健康的人生。正如宋耕在导论开篇引用伍尔夫的那一句名言:「让我们自由无畏地驰骋其间,为自己寻找自我之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作者:邓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