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旅行综艺 《花儿与少年》 第七季开播,网友们再次一哄而上,拿着放大镜去监视嘉宾们在团体相处中的一言一行,龚俊的导游做得如何,陈数作为室友是否 「太事儿」……
这个 IP 自诞生以来就有着超强观众黏性、讨论度始终在线。网友们制作各种短视频,逐帧对比上一季出圈的 「花学」 名场面。
我的朋友 J 刚刚毕业,进入职场后再看这档节目,有了和 「吃瓜」 完全不同的感受,更多是一种 「社会交往」 的分寸学习。和同龄人的对比中,她总是焦虑自己不懂人情世故、「社会化」 程度不够。
她也发现在 00 后年轻人中,这种困窘和焦虑十分常见。
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人把 「社会化程度高」 视为新时代的必备品,甚至夸张地声称:「人生的主线任务就是尽快完成社会化」。
类似讨论还有:「好羡慕那些社会化程度高的人」「不会来事儿是我们的生长痛」「INFP 社会化就像神农尝百草」「可以不世故、不圆滑,但一定要提高社会化程度」……
在一篇十万赞的爆款帖子下面,有这样一条高赞评论:「我们既不想被旧有的人情社会规则驯化,又不得不掌握基本的社交技能来生存」。
J 说,这也是她的想法,社会突然变得好复杂。
为什么年轻人一边抗拒社会化,一边又迫切地适应它?
当我们在说 「社会化」,到底在说什么?
在社会科学里,「社会化」 的定义是:个体在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通过社会文化的学习和内化,逐渐适应社会的过程。
不过,在当下的网络语境里,「社会化」 的含义被进一步延展,被互联网赋予了新的语义。
在社交媒体上,它成了一个流行的 「梗」:年轻人用它来描述初入职场时的尴尬与手足无措,或者在人际沟通中频频 「出戏」、感到疏离的困境。
就像一个 「伪装成大人」 的孩子,突然被推入复杂又难以捉摸的社会系统,在礼仪、话语和潜规则中处处留下破绽。
正如 「偷感」 一词成为 2024 年的年度流行词,这种语境下的 「我」,往往是一个注重自我感受但又无助的年轻人,感受到的是社交中的不安全感。比如:
第一次上班,不知道该在什么场合表达感谢,甚至分不清到底是不是要送礼;
面试时担心自己说多了显得圆滑,说少了又被认为木讷;
公司聚餐里,别人谈笑风生,自己却不知道如何插话。
这些其实都是 「再社会化」 的细节。求学、求职、跳槽……不断变化的环境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学习一套隐形规则,以免被视作 「格格不入」。
因此,所谓 「害怕社会化」,往往并不是抗拒成为社会的一分子,而是对这种持续学习、不断伪装的过程感到疲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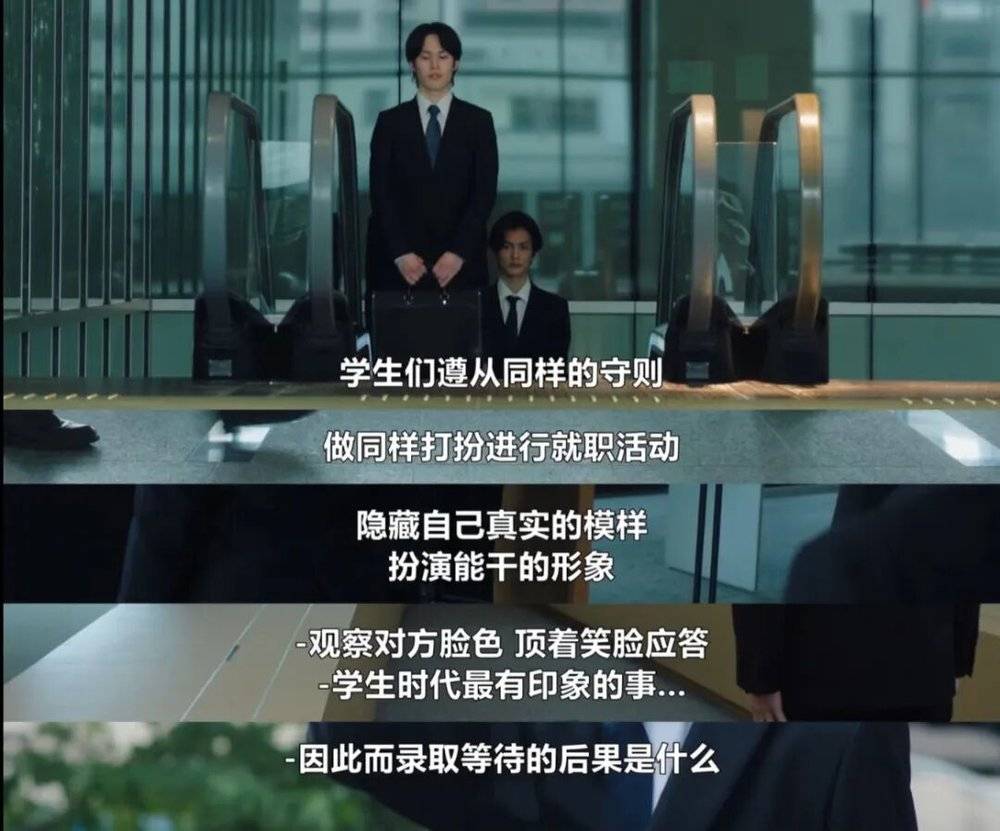
《转职的魔王大人》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自己 「社会化」 不充足?
「不会社交」 并不是少数人的问题,而几乎是这一代年轻人共同的心理负担。
1. 缺乏心理工具:普遍缺失社会情感能力
在教育心理学中,有一个与 「社会化」 紧密相关的概念——社会情感学习(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SEL)。它指向的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需要习得的几种核心能力: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关系技能,以及负责任的决策等方面,学生在青少年阶段一般需要通过项目式学习、团队协作等方式来培养这些技能。
根据 《中国教育报》2024 年的评论,由于社会转型、过度竞争、因使用网络和手机导致的社交减少等原因,当今社会的青少年群体普遍存在社会情感能力缺失的问题。
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教授彭凯平团队追踪了 42 万多名中小学生,发现当代青少年出现了以 「社恐」、缺乏沟通合作能力为主的 「社交无能力」 现象。
这意味着,许多年轻人并非 「拒绝」 社会化,而是缺少了习得社会化技能的机会。发展心理学认为,社会化是需要逐步练习的过程,而在一个催促他们加速成长的社会里,必要的练习场景和心理支持却被削减了。结果是,他们被推到成年人的角色里,却还没来得及为自己装备好应对世界的工具。
2. 向内探索的冲动,撞上了加速催熟的社会
另一个常见场景是:在学校里一路优秀的学生,走出校园后突然发现 「优等生剧本」 路径失效了。学校里的评价体系是透明的,但进入社会后,规则常常是隐性的,它更看重沟通、协作,甚至 「察言观色」 的能力。这些没有人会教,却直接决定你能否被接纳。
这背后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十几年的应试教育让学生们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于是,很多年轻人一毕业,就像突然被丢进社会这个 「大染缸」 里,明明会游泳,却依然觉得快要窒息。
而在增长放缓、竞争加剧的当下,毕业生们也开始被迫提前面对 「我是谁」 的终极问题。同时,这一代人更希望注重自我感受。
社会学家阎云翔提出了 「扩展式青春」 的概念,指出当下的 Z 世代普遍呈现一种 「内在性转向」:他们将人生重心从外部的社会角色转移到内部的精神世界,把自我探索和心理安稳视为人生核心实践。与此同时,经济压力、社会流动受限,也促使年轻人主动推迟了就业、独立居住、婚育等 「成年标志性事件」。
换句话说,当 「长大」 意味着负担和风险时,许多人选择延缓进入传统意义上的 「成人生活」。这种 「拒绝长大」 的姿态,某种程度上加剧了 「社会化不足」 的感受。矛盾也随之加剧。当这两套逻辑相撞时,挫败感几乎不可避免。
在学者看来,我们历经了 「拔根型」 人生赛道、「个性化」 成长模式、「数字化」 日常生活,因此我们出现的 「去社会化」 现象,也是正常的。
创伤与依恋:为什么有的人学得更慢?
不是所有人都能以同样的速度 「解锁社会化技能」,这背后,常常藏着成长经历的差异。
童年创伤,会让一个人更难建立稳定清晰的自我。缺乏安全感的环境,容易让孩子形成 「我是不是不值得被爱」 的信念。这种信念会一路延续到成年,表现为较低的自我关怀水平,甚至在社交中不断自我怀疑。
面对陌生人或复杂情境时,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容易放大负面暗示,结果就是——怕出丑、怕被拒绝、怕不合群。久而久之,这种恐惧甚至可能演变成社交焦虑 (SAD)。
依恋理论也解释了这一点。心理学家 Bowlby 和 Ainsworth 提出,早期和主要照顾者的关系,会深刻影响个体的社会化:
安全型依恋:更容易建立亲密关系,也更敢迈出适应社会的第一步;
不安全型依恋:则可能导致社交中的退缩、焦虑,甚至形成回避模式。
而现实中,许多年轻人的成长环境并不完美:应试教育压缩了情感表达的空间,校园霸凌可能留下持续的羞耻感,家庭紧张氛围更会削弱孩子对外部世界的信任。这些经历,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一个人的社会情感能力。
心理咨询师曾旻在一篇采访中指出,社会化的核心并不是技能本身,而是能否从熟悉、安全的自我世界,走进稍微陌生、充满他人和规则的空间,并在其中保持安全感、建立舒服的连接。技能固然重要——比如沟通、合作、职场礼仪——但如果内心缺乏安全感,即使学会了这些技能,也难以真正灵活运用。
她举了一个例子:孩子刚入幼儿园时哭泣,因为不想离开父母。如果养育者能给予稳定的安全感,孩子就敢走出去探索、与小朋友互动,并在过程中学习社交技能;如果没有安全感,孩子只能被动适应环境,缺乏主动建立联系的机会。换句话说,阻碍社会化的,不是技能,而是内心的痛苦和早年未处理的挫折。
数据也能说明这种困境。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曾对全国 255 所高校的 4854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80.22% 的受访大学生承认自己有轻微 「社恐」;近 7% 有比较严重的社恐;还有 0.64% 已被确诊为社交恐惧症。
社交网络的开放性和匿名性虽然让年轻人有了更多元的线上交往空间,但也造成了线下社交能力的下降与现实离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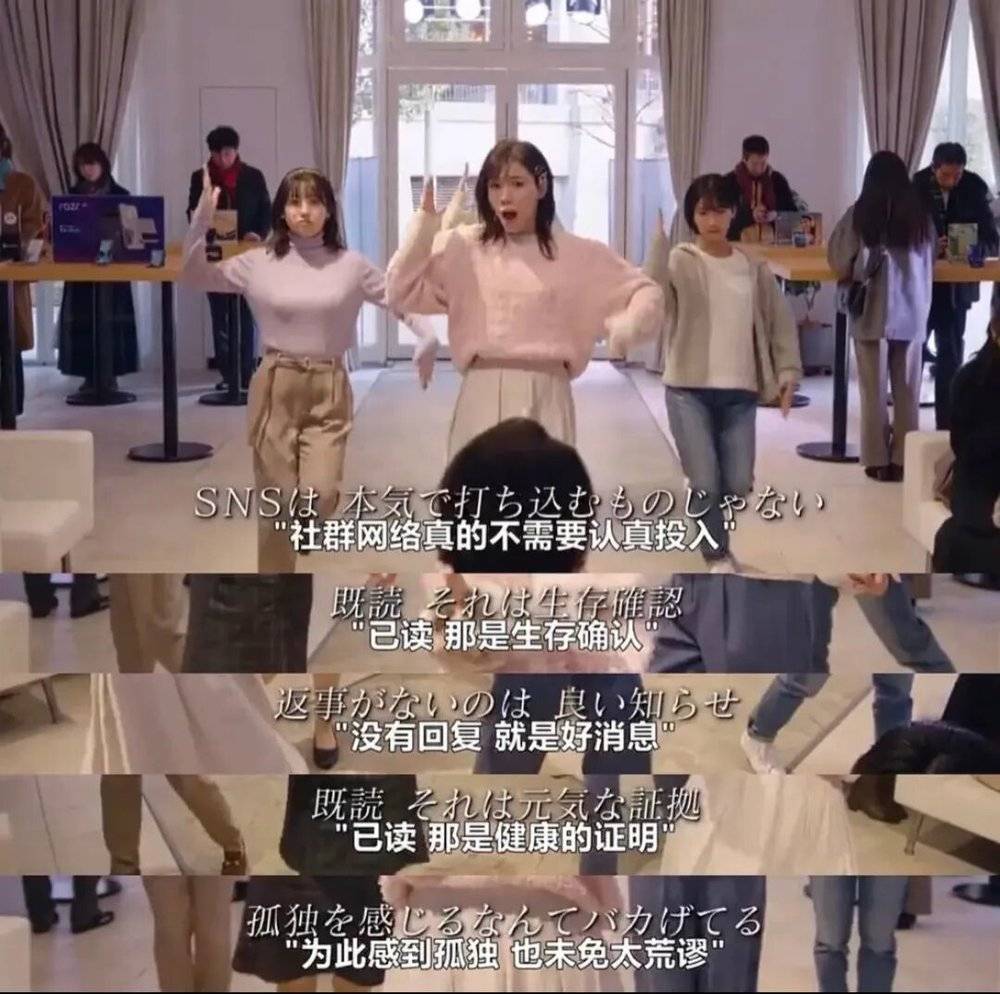
《不合适也要有个限度》
为什么一边拒斥,一边又迫切学习?
1. 更多时候,他们抗拒的是 「异化」
很多年轻人抗拒的 「社会化」,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化,而是被 「异化」 的社会化。
心理学家弗罗姆在 《健全社会》 中指出:适应病态社会并不等于健康。
弗洛姆认为,在异化的社会中,适应社会的人才是 「病入膏肓的人」。当个体为了迎合外部规则而丧失自我主导性,看似 「会来事儿、圆滑得体」,实际上是一种深度异化,这也是上一辈人为职场和人际秩序设计的隐形规则。心理上被社会结构同化,失去了真实的自我。
过度社会化让人产生自我阉割式的安全感:消费潮流化、人际世故化、思想功利化,甚至把同学间的交往视为职场攀升的踏板。
自媒体 「正面连接」 在关于大学生不再拍摄毕业照的报道中指出,现在年轻人们的大学生活中,宿舍里舍友们用床帘和桌帘隔开生活区域,维持着 「圆滑且淡漠」 的关系,与同学则是划分敌我,为有限资源内抢夺优胜而战。
不管是升学保研还是评奖评优,几乎每年都能听到有人被恶意举报的经历。
换句话说,我们反感 「社会化程度很高的人」,不是 「社会化」 本身,而是讨厌被迫成为麻木的、假面的、精致利己的、空心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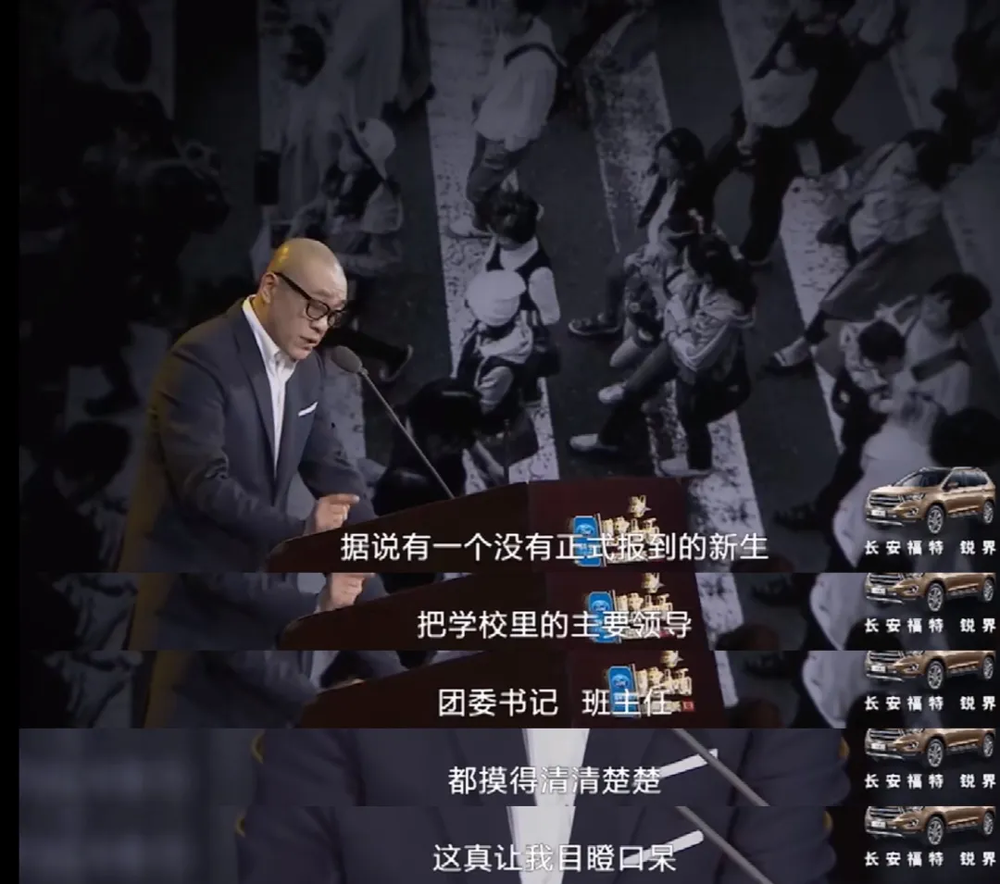
《见字如面》,何冰读钱理群的文章
2. 健康的社会化,需要和他人建立联系
真正的社会化,并不是放弃自我,而是在保持主体性的同时学习与他人建立联系。
社会学家米德在 「主我与客我」 理论中指出:人的自我分为 「主我」(I)和 「客我」(Me),前者是自我对外部世界的即时反应,后者是他人眼中的自己。在两者不断互动中,自我意识逐渐形成。
库利的 「镜中我」 理论也强调,我们通过他人的反馈来认识自己。
社会心理学的角色理论进一步说明,社会化是学习扮演不同角色 (学生、员工、朋友) 的过程。正如设计师山本耀司所说:「自己」 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撞上一些别的什么,反弹回来,才会了解 「自己」。
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跟很强的东西、甚至可怕的东西碰撞,然后才知道 「自己」 是谁。
3. 年轻人该怎么办?选择性适应
当下的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 「社会化」,他们更注重个人生活质量,反思不良职场规则,不再试图融入所有人,而是 「找到同频」 的人。
健康的社会化为什么重要?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必须通过社会经验来学习所在社群的文化,并掌握最基本的生存技能。
正如 《社会性动物》 一书中写道:「在支配社会生活的所有动机中,最重要的是归属:我们渴望与他人建立稳定、有意义的联系。」
这种基础性社会动机意味着:长时间的非自愿隔离不仅会令人感到不愉快,而且在心理上是有害的,会产生抑郁、焦虑和自我毁灭的冲动。感觉与社会脱节会导致人们失去调节情绪和控制注意力、行为和冲动的能力。
而 「那些遭到拒绝的、孤立的学生在考试中的表现往往较差,他们会食用更多的垃圾食品,而且比那些觉得自己属于同一群体一部分的学生表现得更具有攻击性。」
一定的社会化是必要的,但也不需要去羡慕社会化程度高的人,用 「高情商」(EQ)之类的词来衡量个体的成功与否。
哈佛大学的一项 75 年的长寿研究 (HarvardStudy of Adult Development)显示,最幸福的人并非社会化程度最高的人,而是那些能够平衡社交需求与独处时间,忠于自我的人。
最好的策略可能是,人并不一定要被动地全盘接受所有社会规则,也可以选择性采纳社会规则。
社会化并不等于伪善,它更像是一种在 「保持自我」 与 「适应社会」 之间寻找平衡的智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简单心理 (ID:jdxl2000),作者:Kira,责编:罗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