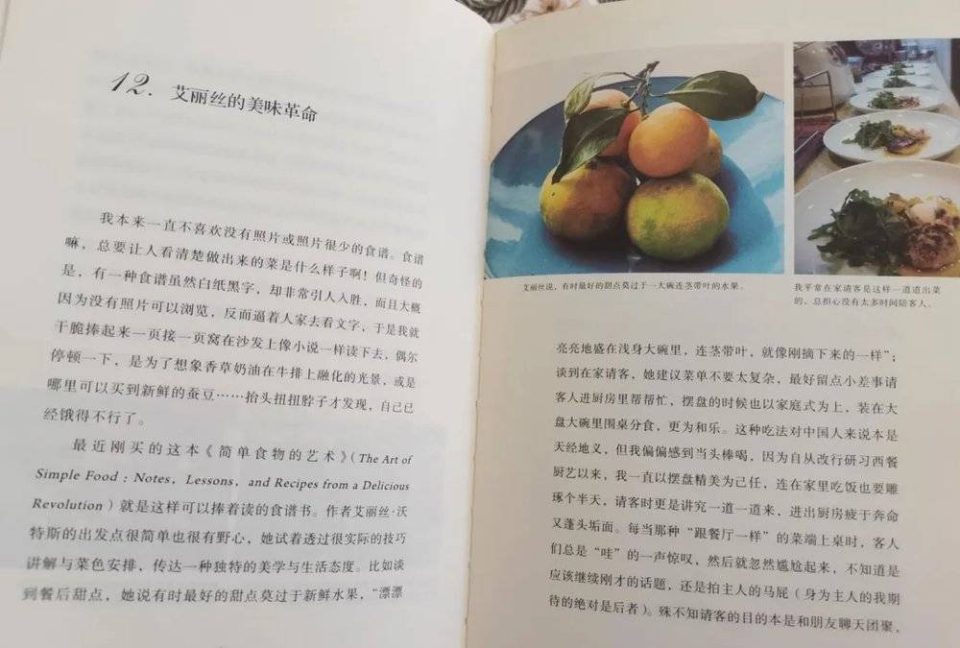本科哲学,硕士人类学,实习做了新闻、教育、咨询,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大厂做 AI 产品经理。我的成长路径歪歪扭扭,处处有风景,处处是选择。
朋友们对我很好奇」 出国留学去读纯文科,是没有找工作的焦虑吗?」「最后又是怎么能成为 AI 产品经理的?是因为坚持了热爱吗?」
我也从朋友们的提问中看到了他们的困惑:如果热爱的、内心真正想做的事情,与现实既定的轨道格格不入,该怎么选择?
也许我可以给你分享一点我的故事。
在最想要反抗世界的年纪,遇到了哲学
我其实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小孩儿,在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教育系统中长大。小学和初中时的我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在学习上,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
我很会做题,并且长期受益于此,于是对应试之外的事情都很迟钝——这些是我高中上了之后觉察的。
我读了 IBDP 一个国际课程,第一节试哲学选修的时候,老师说 「好学生 「是一个标签,正如所有的名词、形容词、社会代号。
我因此找到了一种语言来描述长久以来那些若隐若现、却无时无刻让我不安的疑惑:
我真的想要成为 「好学生」 吗?
如果不用这个标签、不用分数和排名,我该如何介绍自己?
成为 「好学生」 是我的主动选择,还是在被动满足外界的期待?
……
这些想法把我的世界撕开了一道口子,它像泄了气的皮球,偏离了按照既定轨道一往无前的运动。而哲学作为一束光照了进来。
我决定将哲学作为正式的、需要参加最终考试的课程来学习。我觉得哲学好像可以给我一些话语权,一些思辨的能力,让我能够去判断身边各种各样的声音。它就像是我思想上的武器,能给予我精神上的力量。
哲学让我和自己和解了
真正学起来,才发现远比想象中要难。
那是一个大语言模型之前的时代,翻译软件也算不上智能。用不熟悉的英文来读复杂抽象的概念,好不容易弄懂了所有单词,连在一起了又读不懂句子。太容易走神了,我必须用笔尖指着,非常缓慢地阅读。
逐渐,「细读文本」 的过程让我理清很多思路,作者的想法、我的思考,我对观点的判断从简单的对错,变为哪里对、何时错,又逐渐开始运用不同思想之间的对话,多角度地理解所处的世界。
这份收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的高中哲学老师,他曾接受过非常严格的哲学写作训练,对我们也是如此。
他改作业是当面批改的,会一字一句地追问:「你这里没有写清楚,你整个文章的结构清不清楚?每一个论点清不清楚?你举的例子能不能支持你的论点?」 甚至会精细到一段话里,每一句和下一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否成立。
就这样被他 「磨」 了整整两年,我的思维能力有了非常大的提升,学会了如何把一件复杂、抽象的事情给弄明白、理清楚。
更有趣的是,哲学读多了之后,我开始学会和 「好学生」 这个标签相处了。我开始理解那些投来期待的父母、老师,以及同辈压力,这些背后其实都是一些流动的文化符号。
哲学讨论什么是 「好」,什么是 「正常」,当我理解了这些标准都不是锁死的,而是动态变化的,我对于外界那些要求的看法,也就没有那么看重了。
这段经历也给了我面对挫折的勇气。作为一个从体制内出来的学生,第一次申请海外学校,要考托福、SAT,还要写文书,这些我都应付不过来。SAT 我考了三次都没有考出理想的分数,甚至还出现了数学不及格这种以前从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正是哲学在思想上给我带来的 「松绑」,让我有能力去面对这些挫折。
哲学虽然没有让我看透世界,但是让我可以接受每一个阶段认知水平的自己。
开始硬刚,我就要学哲学
到了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因为在高中获得了思维上的成长和精神上的支持,我几乎毫不犹豫地决定继续读哲学。但这在我的家庭里,引起了很大的阻力。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出奇地一致:学这个,将来怎么找工作?
我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大家虽然有这个担忧,但并没有人提供任何解决方案,也没有人真正来关心我,问我为什么要在那个阶段选择哲学。他们只是停留在问题的表面。
既然没有更深入的讨论,那我也就正面 「硬刚」 回去了——我想学,我就得学。
就这样,我进入了多伦多大学。
多伦多大学的本科学分设置非常鼓励学生主修两个专业。于是我在哲学之外,又选择了人类学。Again,是凭兴趣。我读了庄祖宜的 《厨房里的人类学家》,三毛的 《撒哈拉的故事》,还有一些人类学书籍的选段,被人类学这种实地调研+报告文学+社会文化理论分析的学术方式深深吸引。
厨房里的人类学家
与哲学的 「求真」 不同,人类学是 「求实」 的。人类学研究要经历漫长的田野调研,学者去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学习那里的语言,参与当地的生活,了解当地的文化信仰、社会变迁的原因,经济劳动与收入的结构,还有家长里短的琐事,权力结构下的冲突反抗,以及反复看到自己视野中的偏见与局限。
这是一种非常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效率低下」,不符合现代科学的标准化知识体系,它需要身体力行收集大量数据,将心比心地做理论和假设。但是它恰恰能看见真实具体的人,能看见社会边缘化的地界,能看见主流的话语、权利如何流动、变化,生生不息。
我被这种方法深深吸引,并把它用在了自己的研究里。我主导了一项关于 「学校文科写作打分制度对学生多样性影响」 的田野研究。
我在图书馆和写作工作坊中,去看学生们写论文时的状态,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如何寻求帮助的。我陪着同学一起写论文、走神又拉回来、帮忙保管鼠标,所以他们可以忍住不打游戏、去图书馆小卖部买半夜剩下的两盒冷冰冰的寿司、最后还是过了截止时间才写完提交,犹豫着给教授发邮件解释,然后看着自己并不算满意的论文叹气……我趁着期末考试前两周谈了教授、助教、学生们,最紧张的时刻,大家反而很愿意讨论 「文科写作的打分制度」,分享很多真切的想法。
最后,我写出了一份报告。它似乎击中了教授们对于教学的一些理想 「泡泡」,让他们发现了一些自己习以为常的教学方式中未曾意识到的漏洞。我的教授很感兴趣,还邀请我在学校一个关于教学方法论的会议上,向其他教授做分享。
这个研究甚至还推动了一个写作中心,采纳了我的调研问卷,建立了更有效的学生反馈机制。我感受到了人类学的力量,是来自真实与思辨的力量。
从象牙塔走向现实
在本科学习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晰地发现,相比于哲学那种对终极真理的追求,我更关注现实中具体的人,关注写作和讲故事,关注那些社会问题是如何影响人们具体的生活的。
我还做了两份新闻领域的实习,在上海电视台做编导助理,参与制作一部关于上海医生支援武汉的纪录片;在澎湃新闻做实习记者,报道教育、科技发展、城市规划;宏观议题的探讨后,我总是落到对具体的人的关注、小而真的故事,细节总是有力的侧写。
因此,申请硕士时,我的方向转向了新闻和经济人类学两个方向。

在英国喜欢徒步
大三申请时,我带着 「这样转专业该如何准备」 去咨询了 BeBeyond 的 Linda 老师,她说 「这不算转专业,它们本质上是很相近的事情」。
这让我安心了不少。原来 「专业」 不是一个锁死的学科,是系统性的可迁移的认知和实践方法,也是一些灵活的软性技能。
我所学的人类学的田野研究能力和来自哲学训练的思辨能力,也用在了选校上。
我为新闻和人类学这两个专业,各自按排名拉了 Top20 的学校的清单,了解了每个学校开设所有相关项目,找到和我的目标最适配的 Top10 项目,最后按照学校和项目的质量,职业赋能和我的兴趣、资源、成本、他人建议等方面给他们排名,投递了两个专业的前 3 名 (是的我是超级大 J 人),整个过程很顺利。
我最大的收获是清晰地看到了大学在招人时的底层逻辑和决策标准——他们到底想招什么样的学生?什么是 「值得培养的」?
这个框架,让我在梳理自己的学术兴趣、成长经历、发展目标和最终撰写文书时,明确知道每一件事情要呈现到什么程度,因此能够最大化地分配时间精力。
结果也很幸运,我拿到了 LSE 的经济人类学录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的录取,都是我最想去的项目。
面对这个幸福二选一的 「烦恼」,我没有着急选择。
我听了听本科教授们的意见。在哥大完成博士学位的教授和我分享了她的朋友们在新闻学院的学习经历,快退休的人类学教授和我聊了人生的宽度、广度,念书只是一种的一个小小的阶段,所以不必短期拘泥于学校的 title……
同时我在当时的商业人类学咨询公司实习中,仔细实践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商业落地的执行和交付,比如研究 「哪些部分带来了市场竞争力」。我知道我更需要这种现实中的落地检验,来理解和探索这个世界,探索我能做什么,想做什么,成为谁。
所以我选择去 LSE 读经济人类学。

继续徒步
求职求着发现入了 AI 的行
在 LSE 的经济人类学学习给了我完整的分析经济、社会、文化的框架,是收获满满的一年。出于学术兴趣和自高中以来对学界工作的美好期待,我仍然纠结着要不要申请博士。但是现实世界像是严厉的老师,总用直接的教训让我迅速成长,我决定开始找工作。
其实,从本科学习纯文科以来,尽管当时经历了家里的层层反对和外界的许多的不解,我一直不是特别担心自己会所谓的 「找不到工作」。
我关注的是,希望自己有一份能够在其中不断成长,和时代一起发展的工作。不过,我做了五份实习也没有完全弄清楚这样的工作是什么,也不清楚自己是要在国内还是国外发展。
带着这样的迷茫,我仓促地进入了秋招、春招,投递过国内许许多多的大厂、小厂,以及加拿大的许多机会 (因为本科毕业之后,就着政策福利拿了工作签证,我先去了加拿大求职了三个月)。这一年就业缺口小,落到每一个应届生的头上,是激烈的竞争。
但我并没有因此受挫,那段时间,我将求职视为一场大型的 「人类学田野调查」。我在加拿大面试过一家挂着 「市场分析师」 的岗位,去了才发现是去线下推销电话卡和会员卡的公司(那我可得看看平时路上拦下我推销的组织内部是什么样的)。
面试我的印度小哥是小组 leader,非常有激情,尤其是他在画饼、算薪资结构的时候;他一定为他自己能做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寒冬中,这种生命力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也让我看到,加拿大的就业市场和经济前景并不乐观,很多人才都去应聘买电话卡的公司了。
于是我回国参加春招,大厂的机会不太多,小公司的机会倒是不少。注册求职平台以后,我平均两周能拿到一个 offer。出于想要找到最合适的工作,就算是顶着春招快结束了、就业竞争激烈、每放弃一份 offer 就要重新面对不确定性,进入新一轮投简历和面试的流程,我也坚决地放弃了好几个机会。
我相信,只要我不断地拒绝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总能够拿到最适合自己发展目标、最感兴趣想去做好的工作。

求职的时候遇到卡点会去长江边看日落,看看开阔的天地
真正的转折点,是我面试了一家非常小的 AI 初创公司。虽然最终没有加入,但我认识了那位老板,并加入了由他运营的一个高质量的 AI 开发者社群。那个微信群每天都会推送最新的行业信息,成了我入行的关键节点。
我开始主动帮那位老板做一些市场调研,甚至构思一个 AI 笔记产品的想法,并在这个过程中自学了低代码开发。这些实践,对我真正了解 AI 行业和产品设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成为技术团队里的小鲶鱼
最终,我选择加入了一家上市的营销公司,在其 AI 创新部门担任产品经理,负责打造 AI 驱动的视频生成与剪辑工具。这个方向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它既有成熟的业务平台作为基础,又在 AI 创新上有非常坚定的投入。
我的工作内容很充实。从产品的调研与设计,到协同技术与业务团队,每天都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学习和尝试。我们技术团队的同事 「I 人」 居多,他们在开发上非常擅长,沟通方面,我需要来回游走活跃气氛,像一条 「小鲶鱼」。在讲究高效的沟通和技术评估之外,我之前苦练的 「整活儿」 和讲笑话的能力也终于在活跃团队的时候派上了大用场。
我很快发现,过去在人类学研究中积累的访谈、协调、思辨能力,以及哲学训练出的逻辑和写作能力,都在不断实践中迁移到了产品经理的工作中。即使在还不完全了解所有技术细节的情况下,我也能把整个团队要做的事情梳理得非常清楚。
最让我开心的是,AI 的开发迭代速度非常快,我能迅速看到自己工作的真实反馈。我们做的功能,生成的视频,投放出去后能不能成为爆款,这些都会被市场快速验证。这种及时的、落地的反馈,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也非常好玩。
回顾我的经历,其实一直在两条线上走。
一是坚定地选择自己兴趣强烈、目标所在的方向,即使面临质疑和外界期待的压力,也做好手头的学习、工作;
二是在不断走向一个更落地、更务实的过程,从抽象的哲学思辨,到关注具体社会问题的人类学,再到被用户直接检验的 AI 产品,我也越来越看重所做的事情能否在现实世界中激起真实的回响。
文科的价值总在被质疑,正如学习、工作、热爱、现实等所有的事情一样。但是坚定地向前走,世界便会开阔起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BeBeyond(ID:BeBeyondG),作者:BeBeyond